 |
| (2009/1/17三鶯部落抗爭尾牙,右三為陳雪)張榮隆 |
一直以來,我對陳雪的認識幾乎用前面那兩句話就能概括,直到去(2008)年11月底,她在我的部落格留言,表達希望能跟我們討論,一起為三鶯部落做點什麼開始,她的身影就不斷地跟大夥兒一同出現在三鶯部落的行列裡。
去年三鶯部落自救會舉辦抗爭尾牙,她捐出5本著作《橋上的孩子》義賣,觸動我閱讀她的這本半自傳體長篇小說,並奇妙地找出文句間居然跟三鶯部落,有著極為相似的景況。究竟是我無意間翻現她們的相同,還是我強加兩者間的關連?就讓陳雪自己來談談吧。以下的採訪記實以問答方式,並以《橋上的孩子》文句錯落呈現:
江一豪(以下簡稱問):為什麼會想送《橋上的孩子》這本書給三鶯部落義賣?
 |
(2008.三鶯部落部分建物遭拆除前)江一豪攝 |
我們也曾經市場裡住過,就是用很簡單的木板隔起來,連屋頂都沒有的小隔間而已,那個情景就跟三鶯的房子有點像。當初之所以住在那裡,就是為了早上能早一點起來佔位置做生意。當時家裡為了賺錢,我們常住在這種地方,小孩子往往在車上,甚至丟到紙箱裡就睡了。雖然我們並不是窮到這樣,但為了賺錢還債、為了求生存,而有了這種生活樣態。
問:就是這種生命經驗把妳跟三鶯部落扣連在一起?
雪:雖然我後來成為一個作家,但我覺得自己跟三鶯部落在某個層次上是命運共同體。因為我是從這樣一個非法、違法、不該存在的流動攤販的生活經驗成長過來的──我們都曾經是違法的,都可以被開單、被掀翻攤子、可以被抓、東西被沒收。我到現在都還很記得,我們全家在搶救那些被警察摔壞的卡帶的畫面。
當流動攤販,一直是我們家的生活處境,即使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店面,在比較大的日子(編:生意好的時候)裡,我爸爸還是讓我去當流動攤販。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,你永遠都是不合法的,只因為你想賺錢。可是想賺錢背後的許多原因、命題,是有些人不會、不願去理解的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之前女孩跟弟弟妹妹住鄉下老家,
媽媽在台中,爸爸忙起來就住豐原
潭子各個賣場,好不容易有了自己
的店,一家團圓,雖然跟鴿子籠一
樣小,他們情願這樣全家人擠在那
個小閣樓裡生活。
《橋上的孩子》頁167~168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問:所以妳是以「理解」而非「同情」在看三鶯部落?
雪:我很小的時候對世界的想像,就是很多層次、很斑駁的。一個地方可以有高樓、有店面,但也應該容許人是以這種流動、不合法的方式的存在。我企望這個世界可以讓這麼多人因為這麼多不同理由,以不同的生存姿態存在。我並不是說要讓流動攤販都合法,但應該要有這些縫隙。比如說我父母讓我小時候做這些事情很痛苦,可是我相信還是會有人有需要用這種方式存在。所以當初去三鶯,並不是以自己比他們條件好的姿態去關心,而是在遭遇上有著跟他們比較相近的處境,讓我可以很輕易地理解,人往往會被迫採取某種方式存在。送他們《橋上的孩子》,正是因為我可以理解他們,同時也希望其他人可以理解,即使我們不存在同一個生活條件底下,但這個差異應該是可以被看見的。
問:三鶯部落的原住民身分,也是讓妳發生關注的理由?
雪:這個部分是緣於我個人的經驗。我年輕的時候有個很喜歡的人,他是個原住民,也是因為透過他,才讓原住民這個陌生的概念鮮活起來。透過他,我才知道原住民在經歷什麼──包括從他求學、到都市裡來謀生,我是很具體地從他在語言、在文化、在求生這多重的經歷裡,知道一個人怎麼被逼到這個境界,讓他不斷不斷在無法被單一分割的處境裡面,面對整個人被貶值的遭遇。
 |
(2008.三鶯部落遭拆除後)江一豪攝 |
但我不會只把三鶯部落單純地理解成原住民議題,而是都市無法謀生的、違法的,等等多重的邊緣。這就跟我是個同志,性別身分比較複雜、或是中下階層的小孩等等身分一樣,所有被想像成弱勢、邊緣的、非法的,都是少數。我們每個人都是很多部分去拼湊而成,但我們不會永遠都站在多數那邊,而某些人在他身上有著比較多的少數,我剛好有比較多的少數經驗,或是比較邊緣的身分,所以比較能理解他們,比較想把自己跟他們結合在一起。透過理解上的結合,我想要整體地去思考,而不只是人道的考量。
問:當初認識三鶯部落的契機?
雪:之前知道三鶯就是透過苦勞網跟朋友們斷斷續續的訊息,一直到朋友親自帶我們去才算真的到過那裡。那次到部落去就很想跟人說說話,因為光是看是不夠的,雖然不知道能做什麼,但至少該說說話,結果就遇到潘阿姨,很快就能對話。那天天氣非常冷,房子也很破,我們坐在屋子裡也都一直發抖,所以離開的時候,心中比較多的還是同情,整個感覺很哀傷。雖然對於這樣的生活我並不算陌生,但過去我們終究是個體,但三鶯是集體在過這樣的生活,所以就比較強烈地想做點什麼。
問:可是後來有了新的發現?
雪:對,三鶯走到今天,我其實滿意外的,他們做到超出我理解的改變。我第一次去的時候,真的不知道這裡的人怎麼在想、在運作如何繼續住下去的這件事,不可避免的,多少會帶些悲慘的角度來看待三鶯,畢竟政府已經把這個地方弄成廢墟,然後人也變少了、很無助的樣子。但他們的主體性跟創造出來的力量那麼強,有一次我帶香港朋友去的時候,看得好多人,大家又都在蓋房子。當初那種淒涼、混亂的氣氛很驚人地整個被翻轉。到了尾牙那天更不用說,大家都很驚訝,那麼快就蓋起一個舞台,整個過程他們雖然對外界表示感謝,但卻也不卑不亢很有自主意識,我覺得這真是很厲害。
 |
| (2009/1/17三鶯部落抗爭尾牙)張榮隆攝 |
雪:我覺得三鶯部落從原鄉離開到都市,來到這裡這麼久,就像是一場冒險,而這個冒險用這樣的形式停留在這個地方,如果不是政府一直強力的拆遷,我相信這裡會發展出很奇妙的生活方式。像潘大姐在三鶯種菜到市場去賣菜,跟當地漢人都市生活發展出來的關係,其實就是一種冒險,這也是我很能理解、體會的經驗。所以我一直不是從悲慘、同情的角度來看三鶯,我反而覺得那是一種很奇特的生命力的展現。
我常常會在路上觀察到很多地攤,他們都是違法、都是冒險者,而在冒險的過程中,也會開展出很多讓人驚嘆的部分,像現在的地攤很多都是用一個紙箱加上一片紙板就可以做生意,一瞬間就能消失無蹤,跟他們比起來,我們過去擺的地攤真是太麻煩了。看到這種地攤我很喜歡也很讚嘆,雖然他們是違法,可是我很喜歡這種事情,因為這個世界本來就不是固定不動的,而我也不認為只有真正很弱勢的人,才值得用人道的角度被支持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是這個小小的店鋪,好不容易才還
清了債務,接下來就可以開始存錢,
以後或許可以在豐原買一間屬於他
們自己的房子,像妹妹許多次畫在
紙上的那樣,有三個房間,客廳跟
廚房。
《橋上的孩子》頁104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問:合法、非法並不是妳看待世界很重要的端點。
雪:隨著文明的發展,人要住在一個溫暖、舒適、牢固、合法的地方,其實不是皆如此的,這是被建構出來的。在三鶯部落我看到他們所過的生活,不一定是我們所理解的,但不是所有人對生活、對生命的想像都是一樣的。我總覺得,他們想建造自己的生活,那不一定是外面的人所能想像的。
早期我父母讓我過那樣的生活,雖然當初會有些怨懟,但過那樣的生活除了有其必要,對我的生命造成的其實不是負面,流浪反而成為我生命的主題,所以我非常能理解三鶯部落的族人不願意去住大樓。如果他們需要,那應該是慢慢被建構出來,而不是馬上被硬塞到那個地方。
人跟土地的關係,往往超出金錢、法律之外。過去我們家店面門口就常常有個賣爆米花的來擺,雖然擋住我們的門口,可是我爸爸媽媽從來沒有跟他收過租金,還異口同聲地說:因為人家早上三點就來擺,所以不應該趕他。對我父母來說,他有理由「合法」在這邊生存的權利,因為人家這麼多年來,早上三點就來佔,他付出的是時間。
我看到三鶯就是這樣想,不論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,他們在那邊已經居住了那麼久,有許多人用這樣長的時間,把這個地方變成他的地方。他們所付出的時間、精力、他們與這個地方的關係,早就已經超過他們是否合法的這個層面。因為跟土地發生關係,最快的方法就是付錢,但是有些人雖然沒有錢買、沒有在契約上完成這件事,可是他所付出的時間、精力早就超過這個層次。
我就是用自己這樣的經驗來看待三鶯部落。
(未完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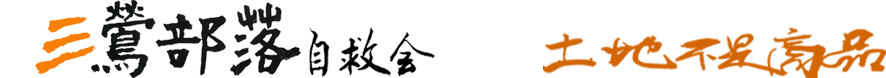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